读柯雪帆教授《疑难病证思辨录》笔记(陈萌)
(一)
上海中医药大学浦东校区7号楼4楼伤寒金匮教研室的墙上,至今仍挂着一幅照片。坐在前排中间的老人就是柯雪帆教授。老人旁边的何新慧老师、吴中平老师、孔祥亮老师,他们的伤寒课我在读书时乃至毕业后,都陆陆续续听过,且吴老师、孔老师的课听过不止一遍,每次听都有新收获。上课时或者下课闲聊时,老师们时而提到柯老,印象中的柯老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为人谦和,治学严谨:自己想不通的问题会主动向年轻人请教,而做学问严谨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个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没有一点传说中老中医的“迂腐”“古板”,对新科技新观点很容易借鉴吸收,与后学新人可以顺畅沟通;再一个老先生敢于“破格”,且十分灵活:吴老师回忆柯老用大剂量炙甘草汤治疗心悸,其中生地用到250克,这样大的剂量药房不肯配,柯老的办法是把处方药物剂量大约减到原来的1/7,配14剂,再把7剂药合在一起煎,问题完美解决。
(二)
个人感觉,在各种文献中,柯老出镜率最高的恐怕是关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物剂量的问题。研究古代中药剂量问题的文献,绝大多数离不开引用柯老的成果,即《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年12期《lt;伤寒论gt;和lt;金匾要略gt;中的药物剂量问题》一文。柯老经过考证,推论东汉时1斤等于现在250克,一两即等于15.625克。《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药物剂量应该以此来计算。15.625,这个数字,印在我脑子里很多年,能开出在许多同道(包括药房)看来“超大”剂量的处方,这份底气的源头,便是柯老和他的文章(以及柯老高徒吴老师的实验与实践)。
(三)
今年上海疫情期间,偶然的机会,和蔡淦老师有多次长聊(在平时忙碌的工作中是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蔡老师多次谈到自己最认可,甚至最“崇拜”的同龄人,便是柯雪帆老。蔡老和柯老是同一届入学上海中医学院,是第一届毕业生,二人一起在曙光医院轮转、工作过好几年。(后来还一同被单位分房分到一个小区:上海万体馆旁 天钥新村“教授楼”。)柯老因成绩优秀,被调到学校专职教学,主攻《伤寒论》。柯老中医理论功底深厚,文采很好,文章写出来很漂亮。蔡老师还让我找出柯老的《疑难病证思辨录》一书给他看,应该算是“二刷”了吧。一段时间后,蔡老师作了一些手抄笔记,给我让我重点关注,对我将来写文章有或许有用。
说实话,《疑难病证思辨录》这本书早在大学时期就买来了,可能是受“章回体医案小说”体裁的影响,觉得有点“不正经”,一直没有认真去读。直到今年蔡老师反复提到柯老,才又勾起我的兴趣。“百闻不如一读”,买来97年初版的三十回本,一口气读完发觉是我肤浅了,我对柯老更是“高山仰止”再进一层。
可惜柯老走的早,入学未曾见到柯老一面,甚是遗憾。花时间做一点笔记,算是对柯老的纪念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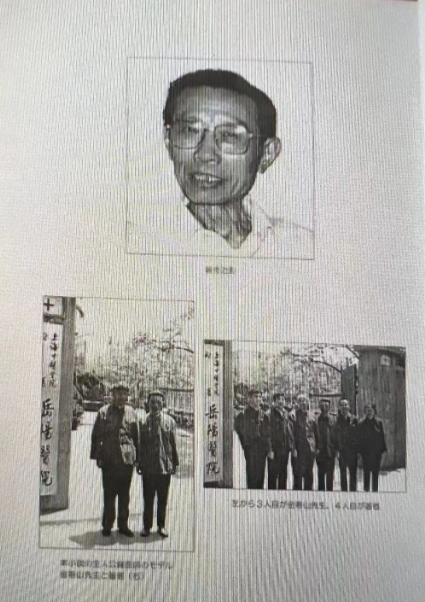
《老中医的诊察室》日文版内封面
(四)笔记
2. “我们今天(治疗萎病),不是独取阳明,而是兼取督脉。对于《内经》我们应该尊重它,学习它,但不能守其制而不变啊!”
3.马钱子加工过程:把马钱子浸软,去皮,切片,在麻油中炒脆呈正黄色,焦黑的与没有炒黄的都去掉,研粉,装入胶囊。早中晚各服0.3克。服后感到口渴、饮水较多、牙关拘急,停药一次,逐渐减量。
4.对五行学说也要一分为二嘛!五行学说的缺点在于对任何事物都来个一分为五,都要纳入木火土金水相生,金木土火水相克的框框;但是五行学说把人体看作是互相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把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看作是有生有克,生中有制,制中有用,这对分析病情、指导治疗都有重要意义。
5.我一生谨守病机,严格按照辨证施治规律处方,想不到今天也因化验的数据而更改用药。化验将要成为中医四诊的延长了啊!把西医检查的结果作为中医辨证的根据,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一种好形式。
6.针麻不仅是一个局部耐痛问题,还有一个全身问题。中医认为阳主动,阴主静。阳虚病人动少静多,有利于针麻手术的进行;阴虚病人静少动多,容易出现不安、烦躁、心烦、汗出,不利于针麻手术。
7.中医不仅要辨证,而且还要辨病。中医辨病有传统,只有辨病,才能掌握疾病的发展规律,才能体现中医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8.我们对各家学说不应该扬此抑彼,不要学徐灵胎老是批评别人,应该学习张仲景博采众方。
9.(眩晕)痰饮上扰者,以泽泻效果最佳,用量要大,至少18克;风痰上扰,首推天麻,退而求其次则为菊花、钩藤;水汽泛滥可用黄芪、防己。用药不必拘泥经方、时方、杂病方,可以随宜选用。
10.炙甘草汤治疗顽固心悸,第一要加酒,第二要加大剂量。东汉时1斤等于现在250克,一两即等于15.625克。《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药物剂量应该以此来计算。——这样大的用量,并非中毒量,而是治疗量。
11.中国有中、西两个医,有两个理论体系,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讨论这是好事。在较长时期内,在总体上要保持两个体系,不要勉强混合。但是,在具体问题上,经过医疗实践,经过科学研究,应该鼓励逐步结合。
12.石决明、牛膝、肉桂三味同用,前人已经用过,并非我的创造。适用于既有阳虚又有阳亢,也是一种寒热夹杂的证候。病情严重的可以肉桂与羚羊角配伍。
13.X线诊断的结果只是反映了病邪留恋的情况,不反映正虚的情况,因而不能作为中医辨证的全部依据。
14.读《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想说明三个问题:一,脾胃气虚是一个基本病因,临床上不一定虚象毕露,而往往可以伴见许多实热之象;二,这个病人不是外感热病兼有气虚,而是劳倦内伤,虚人外感证;三,因此本病用黄芪是为了鼓舞阳气,充实卫气以驱除病邪,而不是治疗一个气虚兼证。所以外邪得除,痰湿内留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黄芪了。
15. 我看用药剂量,除有毒药物要有严格规定之外,一般药物要有较大的灵活性。剂量大小可以根据以下几个因素灵活掌握:首先是病情的轻重缓急,重者急者用量要重,轻者缓者用量宜轻。第二是病邪的新久,新邪宜急攻,要用大剂,久邪宜缓消,可用小剂。第三是病人体质,体质较强者可用大剂,体质弱者,非但不可用大剂攻邪药,即使用补药,也要考虑虚不受补。第四才是年龄、体重。
16. 对十八反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反药能用,属于相反相成,但反药不可滥用,其中有些药本身就有毒性,临床应该谨慎。
17. 近年来,有些病人既用西药又用中药,因此出现新问题。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1.这种疾病的常见症状有哪些?哪些症状可能被掩盖了?2.所服西药有哪些副作用?现在出现了哪些?3.目前的舌象、脉象如何?目前还有哪些主要症状?4.将以上3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18. 开丸药方,在制剂方面应该注意几个问题:丸药方中的药物,一要体积小,二要容易研磨成粉。如果要用质地粗糙、体积较大的药物,可以煎成少量浓汁,拌入其他药粉之中,药渣弃掉,不入丸药。铁质、石质药物一般不宜进入丸药。如必须用这类药物,应配以大量帮助运化的药物同用。入磁珠丸中有磁石,就配以大量的神曲。有些药物不易研粉,但可以打烂成糊;有些药物可以炮炙炒脆之后研粉。
(五)
柯老退休后又陆续增补,最新的《疑难病证思辨录》是增订评释本,更适合阅读学习。柯老还是《伤寒论选读》六版教材的主编,也因为柯老,这本教材仍然是历版伤寒论教材的“另类”,可以说是最尊重原著最符合临床实际的一本教材。在历史长河中,能搞清楚一个学术问题就可以名载史册,而学识渊博的柯老值得我们铭记的,绝不止一点两点。把柯老的东西继承好运用好,也是对柯老最好的纪念。
2022.7.10上海中医药大学
关联词条:
版权声明:
转自 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公众号 作者 陈萌
发布评论:
全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