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位中医大夫陈其昌的佛医之路(李铁华)
民国时期有多位名叫陈其昌的男性公民,其中两位与中医有关,一位是河南省获嘉县后寺村人陈其昌(1855-1938),字兆隆,著有《湿症发微》一书,对湿症一门独有研究 [1]。另一位即为本文所述及的民国江苏松江(今上海)人陈其昌。陈其昌(1889-1968)[2],号惟心,晚署独龙老人,佛教居士,出身中医世家,是民国时期佛教社会医疗救济事业的重要推动者。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推广新中医教育,编辑推广姚心源氏《三部脉法》,晚年被聘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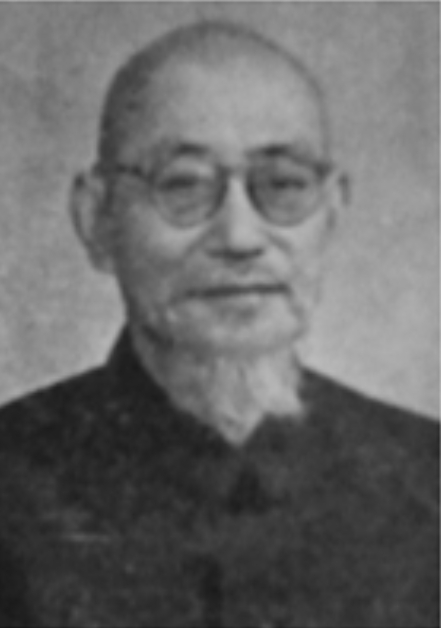
近年来,吴平 [3]、李铁华 [4]、何昭旭 [5]、明满成 [6] 等学者,对陈氏创办的佛教组织及其参与的佛教医药慈善等事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尽管医药学界的相关辞书、文献考证中也对陈氏有所提及,但对他所从事的医事活动及对中医学发展的贡献却考证不多 [7],而且其中还有错讹 [8],如有一些中医辞书和文献研究类的著作将《肺病根治原理》一书的编著者张冠李戴为撰著《湿症发微》的河南中医陈其昌[9]。鉴于此,本文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力图对陈氏的生平和医事活动进行考述,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揭示一个并不显名于20世纪中医界的医者对推动中医发展的努力。
依据目前掌握的相关文献资料,陈其昌一生的经历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热心革命,力倡实业救国;第二时期,实业遇挫,求革心之道于佛教;第三时期致力于改进中医,研究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现分别将陈氏人生的三个阶段做简要考述。
1.热心革命,力倡实业救国
曾任民国初徐海淮扬道尹的王曜在《陈惟心居士略史》一文中云:“幼怀大志,慷慨不群。逊清之季,居士弱冠,愤国事日非,外侮频促,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时革命之说沸腾全国,辛亥岁,钮惕生先生于松江设军政分府,以抗清庭,居士佐助之,并任沪宁北伐义勇军司令。家故饶裕,军费皆自己出,毁家救国,豪侠足风。”[10] 由此可见,陈氏虽出身于中医家庭,青少年时期的志向却并不在行医济世。1911 年反清革命形势高涨,正在学校读书的陈氏,20岁左右,怀济世救国之志,与宰忠汉等热心革命事业之青年人发起组织沪宁北伐义勇军 [11]。民国成立后,陈氏曾留学日本,不久即回国参加全国工商会议,立志实业救国。先后在上海等地参与或发起组织五族少年保国会 [12]、民业银行、民业锡湖铁路 [13],但终因时局动荡、经费困难、他人诽谤[14]、列强干预和官府不信任[15] 等,先后皆以失败告终 [10]。后曾任职于厦门运副公署,但因眼疾而去职 [16]。
2.实业遇挫,求革心之道于佛教
3.改进中医,研究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
陈氏出身医学家庭,其父陈叔廉(1866- 1932),字铭,号九峰樵子,曾患肺病近二十年,屡投中西医药无效,时愈时发,因之披阅《黄帝内经》,总结出一套预防治疗肺病之经验。民国九年(1920)在上海英租界爱文义路创办中国肺病医院并任院长,著有《灵素肺病通论》一书 [18]。陈氏受其父影响,自幼即习医,后因实业救国之志受挫,遂立志以医济世。1917年前后,陈氏始寻师访友,切磋揣摩,曾先后跟随前清太医院院 判王汉臣,天津名医张锡纯,上海和平医社社长姚心源等学习中医。此后,陈氏即委身于中医学的研究和诊疗实践,曾先后充任平汉铁路医院中医科主任、平绥铁路居士林卫生部主任、中国肺病医院院长、中国经济信用合作社医药顾问、上海市中学校医药顾问等职,在松江、上海市区开 办诊所,创办上海佛化医院 [19]。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陈氏不与日伪合作,停办上海佛化医院,避难苏州,与姚心源医师一起精研医学,编著医书 [20]。抗战胜利后,陈氏返回上海,除继续编著医书,还力图复兴上海佛化医院及中国脉学改进会,亦曾尝试编辑医学期刊、创建药厂、举办新中医讲座等推动中医学发展之活动 [21]。新中国成立后,陈氏继续编辑刊印中医书籍,实践推广姚心源氏三部脉法,1962 年被聘为上海中医文献馆馆员,直至 1968 年在上海去世 [21]。
纵观陈氏一生,早年热心革命和实业救国,也曾致力于佛教弘法事业多年,但就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和贡献而言,还是在研究和实践中国传统医学。
1.精研医学、著书立说,阐述医理
2.创办诊所、医院、药厂等医药组织,积极服务社会
3.编辑医刊、举办讲座、创办医学院,力倡建设新中医
陈氏先后编辑出版多种医学报刊,如《医药常识病家福音合刊》《中医防痨运动专刊》《新中医世界》《和平医药报》等,还在《申报》《大生报》《丹方杂志》《现代医学杂志》等报刊上阐述其对疾病、药材、中医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如陈氏所编辑之《医药常识病家福音合刊》,有一“医药常识专栏”,通过对话的形式,论述了民间医药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中医应重视对民间实用医药经验的挖掘整理 [29]。又如其编辑发行的《新中医世界》,宣称要“改进中国医药成为科学化,发扬中国医药广为世界用”,“纳世界知识于中医,广中医学术于世界”,“以期完成中医建设之新局面,深入民间,推行世界”[30]。
陈氏还举办中医讲座,创办新中医学院,复办姚心源氏所创办之中医脉学促进会,编印中医考试进修教材,传业授徒,号召中医界共同研究,以期推动中医革新。1930年代,他即在上海佛化医院举办中医讲座,邀请龚醒斋讲《中国按摩术在医学上之地位》,姚心源讲《三部脉学》。陈氏多年学医行医后,对中医界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他在《中医考试进修必读•自序》中云:“近来中医,水准不一,高者固有而低者亦多,新者太新而旧者仍旧,其故大都由于师传其弟,父传其子,苦无标准教本耳。”“乃将标准原则,临床认识,三焦通义,诊断学,方剂学、药物学,六种。并附以考试须知,临时约法等类,先行出版,聊作考试之津梁,进修之门径,庶几温故者既可以知新,浅尝者亦可以深造。”[20]12 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创办新中医学院,举办新中医科学脉法讲座,吸引了全国各地一批医学爱好者跟随其学习中医学和三部脉法,如高邮陶秀之、上海张云谊、定海周大成、绛县胡福海等。解放后,仍不遗余力在上海开办“陈其昌中国哲学医学讲座”,宣传推广三部脉法,培植医学人才 [31]。
4.施诊送药,热心社会医药慈善
陈氏在《佛医新建设创刊宣言》中云:“佛、医两大因缘,本为我家世世相传之秘宝,而亦为救世救人之大道也。其昌负此佛、医两大使命,卅余年于兹矣。”[21] 陈家世代信佛从医,受佛教慈悲救世和福田思想影响较大,其父九峰老人在世时,即“勇于仁济”,在其创办的中国肺病医院中,对赤贫之人“送诊给药”[32]。陈其昌继承乃父之遗志,早在民初(1912)担任上海五族少年保国会会长时,就与同人筹设戒烟会,对贫民实行免费 [12]。后来从事医学研究与诊疗实践,更在其创办的诊所、医院中为贫病之人送诊给药,尤其是对于佛教信徒则给予完全免费 [33]。如1935年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向玉佛寺、国恩寺、极乐阁的法师施诊送药一百多次,向其他会员送诊一百多次等 [34]。他亦曾与崇信观音同志会、中国放生基金会合作,共同捐出药资和诊金,以优待券的形式向社会上招募或赠送,以达到为贫病人员送诊施药之目的。《申报》上更是多次登载有陈氏向灾区和战事受伤人员捐药捐款的事迹 [35]。他还通过多种方式向全国各地赠送其自制之其灵丹、救苦水等药物。
陈氏出生于清末,成长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年生活于战乱频仍时期,晚年又经历了新旧社会的转换。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人一样,他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又深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一方面保持着传统士人的济世救国情怀,另一方面个人的理想和追求又常常被激烈动荡的时局粉碎。只有不断地调整自我,适应社会的变迁,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并实现自身的价值。陈氏由于家世关系,由革命、政治而转向佛教和医学,并最终把自身的价值追求落实在了推动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上,当然这种传承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1.兼采诸说,民间医学色彩浓厚
2.钻研脉学,保存和发展了姚氏脉学理论
就陈氏的医学研究而言,他在脉学方面钻研最勤,对姚心源氏《三部脉法》的编辑校订和刊印为后世保存了医籍。姚心源氏针对西医对中医脉法的质疑,经过近20年研究后于1930年提出“三部脉法”理论,后由陈其昌、张子英各自于1930年到1950年开展了相关的研究与推广,后被称作脉学复古运动 [36]。比较陈、张二人对姚氏脉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出,虽然陈氏在传承创新方面略逊于张子英,但其对姚氏脉学理论的保存则更为完整和系统,这大概是因为陈氏后来一直跟随在姚氏身边,直至姚心源氏去世,与姚氏有更多的切磋琢磨,而张子英氏则于抗战爆发后一直辗转于湖南、贵州等地与姚氏的联系完全中断 [24]20-21。因而,陈氏先后编辑出版的关于姚氏的脉学及其他著作较好的保存了姚心源氏的论著,对我们研究姚心源氏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及脉学复古运动有重要参考价值。
3.才高意广,各类医事活动缺乏持久性
4.医佛互融,借医弘教与借教扬医并重
关联词条:
版权声明:
本资料为网上搜集转载,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与本网站联系,本网站核实确认后会尽快予以处理。本网搜集转载之作品,并不意味着认同该作品的观点或真实性。
发布评论:
全部评论




















